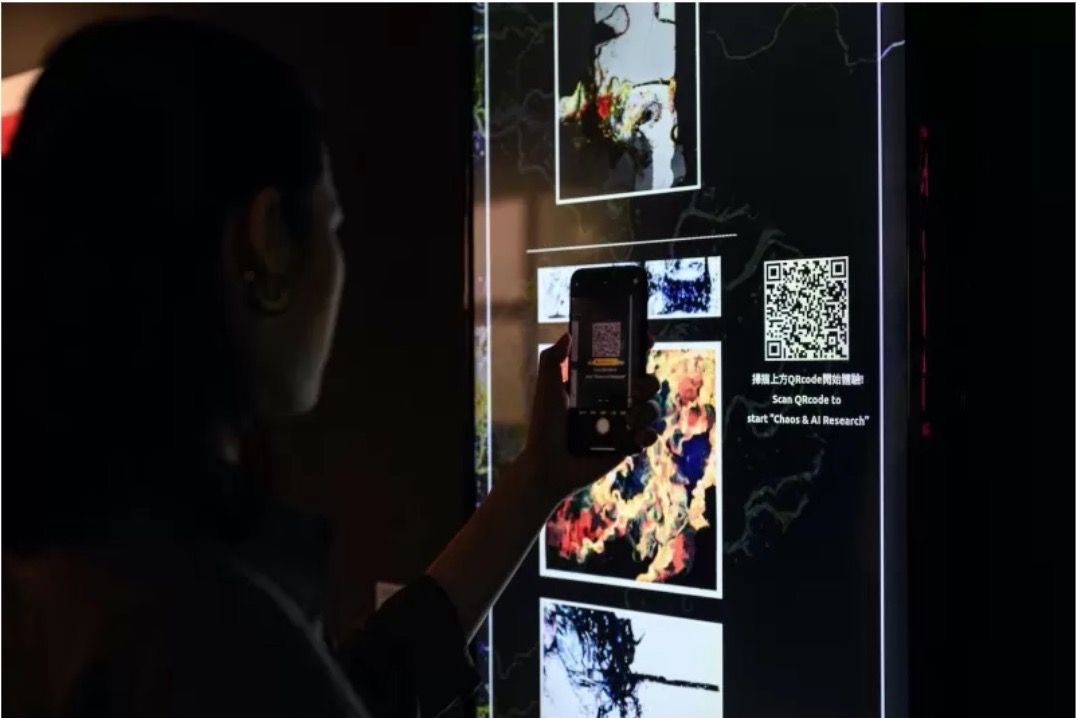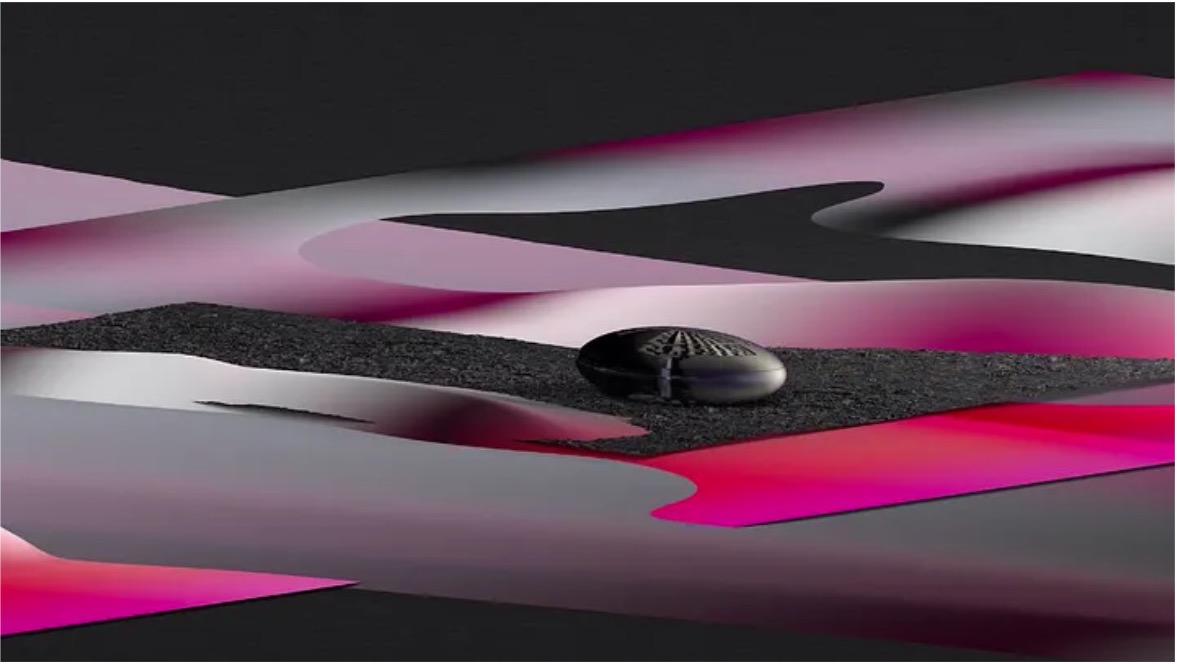作者∕陳寬育
近年,在科技藝術創作與當代藝術策展領域均有活躍表現的羅禾淋,其專業背景與創作思考其實歷經許多轉折與挫折,也在這些豐富的經歷中有對於動畫、設計、程式等領域的獨特心得,現亦積極地以策展的方式展開對當代媒體文化的批判性思考。
Q:請談談你何時開始藝術創作生涯?是否有值得一提的人、事、物的影響?
羅:我以前其實不是藝術背景的,大學在動畫與遊戲軟體設計系中主要是做動畫或遊戲軟體,不過這還這得從高中說起。高中的時候因為韓國的線上遊戲風靡臺灣,因為沉迷線上遊戲,所以常翹課去網咖,玩的遊戲就是天堂。也因為很喜歡線上遊戲,就想著未來要從事相關行業,卻也因此發現有些遊戲的細節實在做得不夠好,於是有了些想要克服遊戲與設定的想法,這包含電動遊戲跟主機的遊戲;最後甚至決定畢業後就去遊戲公司工作。臺灣那幾年也陸續成立一些遊戲相關系所,而我後來念了臺灣第一間成立遊戲相關科系的學校,就是傳說中的18分大學: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大學時學習製作動畫跟遊戲,也出版了兩本遊戲程式相關的書。但後來覺得當時臺灣的遊戲界缺乏原創性,大多不願組團隊來研發自家的遊戲,而是方便地付授權金買進;即使是現在,這現象甚至更加離譜,因為中國大陸的遊戲也進入臺灣市場而且授權金更便宜。可以說,現在遊戲也成為一種速食文化,只要新的遊戲一引進,封測大家玩膩了就換新的遊戲;整個環境已經變質了。
這些現象讓我在大學即將畢業時,就開始思考也許應該要多研究「體感科技」,也報考了北藝大科藝所。考科藝所的原因是想進行不用搖桿、鍵盤或滑鼠進行的遊戲性的技術,而2007年當時還沒有Wii和X-Box360等遊戲硬體,所以對於「體感科技」感到新奇且充滿興趣。但因為大學學的是軟體、程式、特效軟體、動畫軟體,在科藝所才開始接觸了包含電子電路、動力機械跟馬達等偏硬體的東西。以我自己的背景來說,一開始發想作品會跟藝術較無關連,直到慢慢開始接觸哲學、美學的思考,也逐漸修正成比較具「藝術形式」的作品。
Q:這樣說起來,科藝所哪個老師或課程影響你最大?
羅:陶亞倫老師跟袁廣鳴老師對我的影響都很大。進科藝所後第一個看的展覽是當代館的「V2_特區」展,那時我還完全不懂藝術。前往看展時我搭了袁廣鳴的車,儘管我們在車上聊了很多,但我開口第一句卻是問:「老師你是做什麼作品的?」、「老師你結婚了嗎?」等大家會覺得很白目的問題。當然也聊了藝術跟設計之間的關係,因為自己的設計的背景讓我經常用「產品」的方式思考,而藝術某種層面也要用行為設計的角度去執行;在與袁廣鳴相談後,我開始比較精準地知道藝術與設計之間的關係,那一次的對談讓我印象很深刻。
另外,我的興趣在動力機械與裝置的層面,因此主修老師就比較偏向陶亞倫,陶亞倫會用很委婉的方式提點作品的問題,某種程度也慢慢開始影響我的創作方向。
Q:經過這些經歷與思考方式的轉折,一路走來,是否也有哪些欣賞的藝術家呢?
羅:最欣賞做〈仿生獸〉的Theo Jansen。國內的藝術家我很喜歡陶亞倫的作品。他早期的作品比較有禪的味道,到後期使用雷射的作品他開始想要產生出某種奇觀,而到了今年又回歸到詩意性的作品,我覺得他每個階段的作品都有其精準度。
Q:為我們回顧一下你的創作歷程與作品發展的脈絡,以及創作是否有持續關注的面向,或者是關注對象的轉變;無論是題材、作品類型或是文化現象都可以。另外你這些年也做了不少策展的工作,也聊聊這個部分吧。
羅:剛開始因為轉換領域的關係,所以不太知道怎樣去發想一個創作,那個時候老師建議回歸自己,思考生命中衝擊的經驗。對我來說,最衝擊的經驗就是高中那一段時間,我沉迷遊戲到現實世界跟虛擬世界的價值觀是重疊的,已經分不清許現實與虛擬之間的關係;所以早期的作品幾乎都是在討論現實與虛擬何者為真。像是第一件作品〈曲扭效應〉就是個很扭曲的雕塑,透過動力裝置不斷的旋轉,並利用公式計算雕塑在攝影機中的截取的影像,進而形成一個正的佛像。儘管在物理空間中是個抽象的東西,但解碼到虛擬空間中則是一個佛像;當然這會有點向白南準的〈電視佛陀〉致敬的意味,不太一樣的是白南準的佛陀是類比時代的事情,只是我有刻意把數位時代中很重要的編碼跟解碼的觀念加進作品中。
我覺得現今的數位衝擊是很可怕的事情,像是數位頻道跟數位影像的畫面,都是將一些資料結構用點陣的方式顯現出來,但那些資料結構真正的涵義是什麼我們其實不知道。類比起來有點像是二戰時期的心戰廣播,使用低頻的方式一直播放「國家萬歲」之類的訊息對人民洗腦;而數位文化其實也很類似,因為資訊的背後我們也是看不到。
第二件作品叫〈漩渦〉,結構是一個很簡單的空心圓筒結構,你可以將身上任何物件擺進去,物件會被扭曲,那些你熟悉的物件所顯示出來的圖像,是似曾相似卻又陌生的體驗;而且作品也刻意讓空間的資訊採取投影的方式呈現,看似2D但資料結構卻是3D的。所以可以說,這些早期的作品都是在談虛擬跟現實之間,以及數位資料編碼與解碼的問題。
Q:目前有沒有正在進行的作品,或現在策展、創作時特別關注的主題。
羅:前陣子在新樂園策畫的展覽反是談「反媒體壟斷」,這展覽想要讓新樂園的會員與非會員之間可以交流並產生對話的可能。做為展覽主題的新聞事件是2012年8至9月間的事情,現在已很少人還在討論,顯示出媒體亮點的快速性跟速食性。這展覽同時有很多新聞事件的「亮點」,例如展覽當時是駙馬爺的人魚線、北韓射飛彈、于美人家庭事件;到了現在則變成是毒澱粉等,每個時機都有很怪的亮點。因此,當時我刻意地策畫容易「被遺忘」的主題,挑選的藝術家也多是舊作。當一個被遺忘的議題與被遺忘的作品都擺在一起,這就像是一種遺忘的矛盾吧。
更之前的策展是在關渡美術館的「超時空要塞」,主要討論媒體跟網路時代的問題,也特別關注「網路移民」。你我這一代其實都是網路移民,也就是都經歷過有網路跟沒網路的時期,像現在剛出生的小孩就有網路跟智慧手機,所以他們就是網路的原住民。因此「超時空要塞」的展覽概念就是,我們這些網路移民因為網路變成光速衝擊的現象。跟「媒體」議題有關的主要就是這兩個展覽。
另外像在寶藏巖的兩檔展覽都是想談「都市」,分別是「微共鳴」和「廢墟X都市X怪談」。前者想談的是鄉愁,我們可能在都市化的過程中,像是一個有殼的蝸牛但卻不斷的遷移,有點遊牧的感覺,這之中都產生所謂的鄉愁。然而不管居所怎麼換,換的地方一定跟之前的住過的生命經驗有關係。當時展出的地點保留了很多住家的感覺,讓藝術家實地創作與自己經驗共鳴,所以才稱「微共鳴」。至於另一個主題「廢墟X都市X怪談」,則是從微共鳴延伸出來,將鄉愁延伸為文明病,也包含一些都市傳說。
另外還有一些是以動畫為主的策展工作,這算是我很熟悉也一直在研究的領域。在研究所時一直有試著策畫「動畫影展」,主要也是進一步學習策畫與運作展覽機制。後來公部門也找我策畫動漫相關的展覽,我想動漫展當然就會比較具有商業性質,而公部門也會較在意實質的參觀人數;所以我通常會找一些線上很紅的動漫師、漫畫家、CG繪師等,並以比較像商業展的方式進行。
比較特別的是,2012年的「桃園動漫節」我策了一個「如果阿宅讀了德勒茲」展,找了很多當代藝術的作品放在動漫展中,老實說這些藝術家對動漫迷來說,只是「有皮但沒有骨」,所以我就試圖顛倒這樣的情況,找了本來就很宅的動漫迷,但也是當代藝術家像張立人、許哲瑜、周代焌、蘇育賢、陳依純等,展出他們那些跟動漫完全沒關係的藝術作品。這些人在平常談話中就可以知道是很宅的動漫迷,但現在展出較嚴肅的當代藝術作品,這在商展中是頗具衝突感的。當動漫展的一些COSER跟一些GK模型女性角色會被認為是色情,但參觀動漫展的群眾看了張立人的〈古典小電影〉時,我觀察他們對於「裸露」的看法,其實他們對於張立人古典美女的裸露,反而又覺得很正常。
Q:接著也請從你的創作與策展生涯中,獲得的各種形式的支持經驗(包括學院資源、各種獎項、展覽補助與邀約、國內外駐村、各種形式的國際交流等),談談你們對於臺灣目前數位藝術或科技藝術的發展現況的看法。
羅:在臺灣的藝術環境中,對於科技藝術和當代藝術的領域認知還是有點區隔的,兩者重疊的部分主要是錄像藝術跟動力裝置。我想起某次在中國參加的座談會中,曾問策展人顧振清關於「中國大陸的新媒體藝術與當代藝術之間有什麼分別?」答案是這兩者在中國大陸兩者是沒有什麼明顯區隔的。最實際的部份就是中國大陸的新媒體藝術作品也可以像當代藝術一樣地進入市場;但臺灣就完全不是這樣。以臺灣的情況來說,當代藝術與科技藝術這兩者只有我前述提到的一些重疊,尤其是錄像。
至於提到參加國外的展覽經驗時,其實會感覺到臺灣有著相對的弱勢。例如2009年參加巴西的電子藝術節時曾跟當地的藝術家聊,才了解其實巴西在展覽的藝術家徵選方式上對「國籍」這件事還算蠻中立的;相較於此,例如奧地利電子藝術節就比較會因國籍來決定錄取機率。對我們來說最實際的狀況是,當有很多中國大陸的評審時,也就會影響臺灣藝術家的錄取率。
最有趣的是,後來發現很多國外的新媒體藝術家會去讀奧地利的學校,報名的時候國籍欄位就填奧地利,而不是祖國的國籍,這是我覺得在國際上會遇到最實際的操作上的問題。但其實相較之下,臺灣的藝術環境我又覺得比香港、新加坡好很多;像香港以前是英國殖民地,在很多新媒體藝術相關的展覽中,香港籍的藝術家往往只有少數幾名,其餘的都是外國籍的,所以香港的新媒體藝術家也是很辛苦,在那邊還是比較偏好國外藝術家的作品。
此外,我也發現在很多歐美國家,那些年紀跟我們相仿藝術家已經是大學的講師或是教授了,他們認為你有很好的經歷跟作品就可以在學校任教,不一定需要博士的學歷。這些是我目前想到的一些問題與經驗,但只是些簡單的分析與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