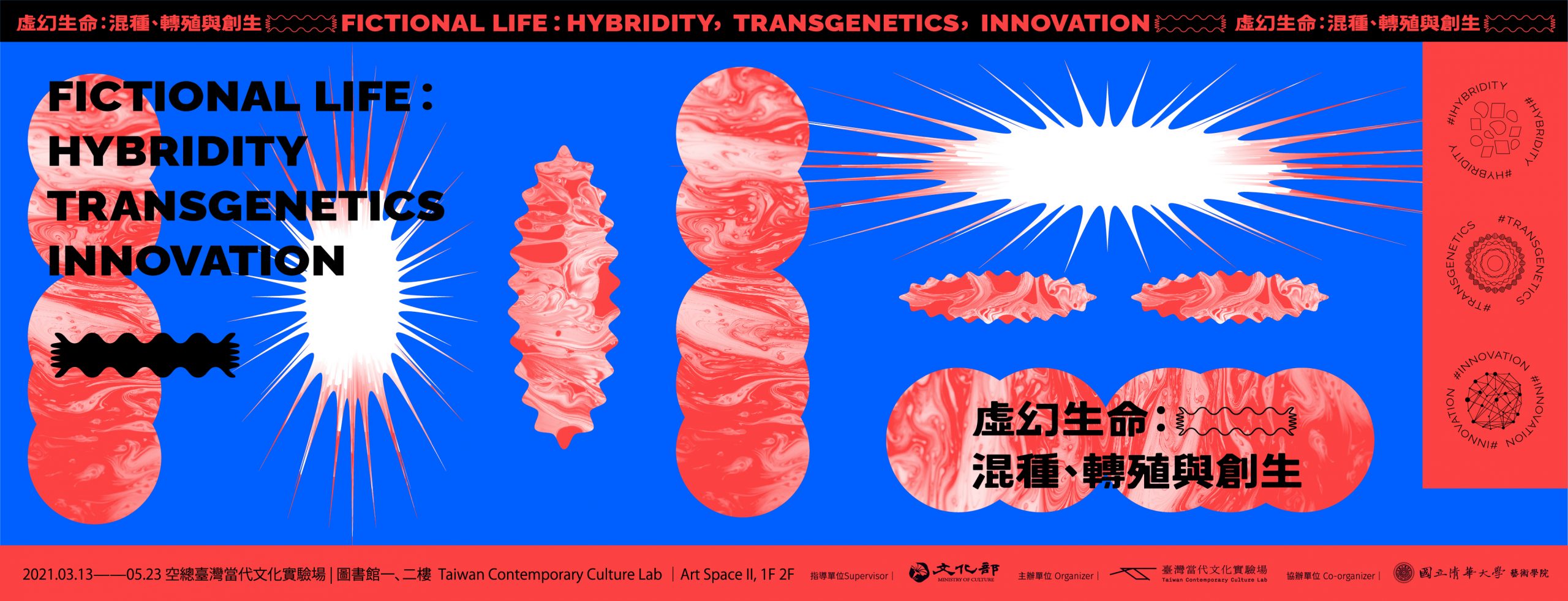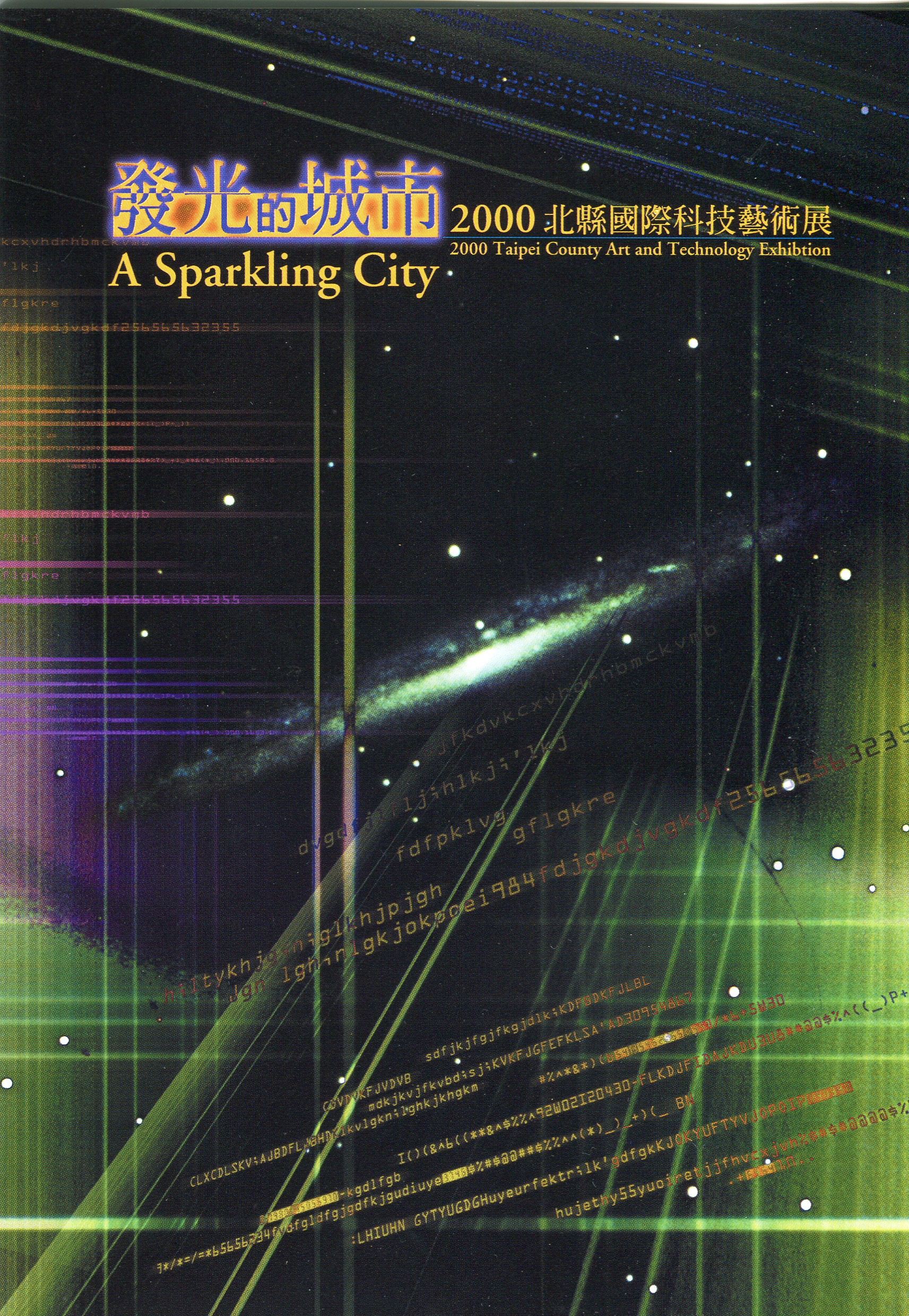
「發光的城市—2000北縣國際科技藝術展」畫冊封面
圖片出處—https://www.deoa.org.tw/project_content.php?res_no=17&cate_no1=&cate_no2=&ProjectYear=
展覽策劃/王品驊
數位時代所面臨的日常生活,許多時候與速度有關,由於整體社會對於速度的掌握慾望和慣性,致使個體在各種問題之前,都應該發現對決的敵人,其實是整個社會運作機制所掌握的「時間」,而面對的方法,往往只能是複雜縫隙間的、瞬間發生的「準確」—一種尚無法形成脈絡描述的直覺。
因而「虛擬」所帶給我們的基本問題之一,竟然可能是對「存在」重新認識的迫切性。 2000.10.10
技術、速度和消費結構等三方面符合人們期待的鉅大進步(並非失敗),創造了20世紀社會文化的發展方向,以及奠定了21世紀再次躍進的基礎。然而在此躍進中,社會文化的多層面也充分感受到,來源於科技的強大「物質」能量之潮,所帶給人類融合炫目「幻想」的希望和潛在陌生焦慮的矛盾體驗。
在本文、本展覽之前,筆者已嘗試在幾篇文章中 [1],將藝術的「觀看」回到認知方法的本身進行美術史歷程的、科學的、哲學的思想方法的比較,透過粗略的思維意象模型,發現20世紀的認識思想從線性邁向非線性、從單一結構邁向開放結構的總體現象,這些相關討論的必要性,是為了探討所提出的展覽核心意象—當代藝術中浮游生物般的主體風格,形成過程的社會文化變遷內涵及其潛在的方向。更重要的是,一種基於後現代對話的開放視野,表達語言的跳躍性和替代性格,如何在「高速」的思維連結過程中重新結組,恢復「表達」的清晰性和單純傳達的「力量」?將是置身「此刻」的一種說話方式。
虛擬世界的形象邊界
藝術語言所創造的「虛擬世界」,如果從內容的本質來看,其實是非常古老的語言方式。從文學開始的各種詩和神話, 就是以語言描述,建構「有效的」虛擬世界,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一開始就說:藝術所虛構的世界,比現實世界更真實更完整。在這個意義上,虛擬的世界,來自一個原本「潛在的」世界。
虛擬的世界和真實世界的差異,如果我們以「變形」來描述,這個變形當然和「觀看」的工具有關。前已有一篇展覽導讀的文章,對於歷史上每個世代的文化母體,都隱藏著一種反應其特定社會文化條件的「觀看」認知狀態,做了描述。每個世代文化,都各有框架限制的認識和描繪「世界」。「觀看」的工具有如一面鏡子,我們今天已經學到,我們不僅透過鏡子看世界,同時我們必須反覆反省這面鏡子。鏡子中的「世界」何時真實過?我們不僅要問,同時要學著接受—答案從來不在鏡子裡。英國美術史學家貢布里希,在《藝術與科學》回憶錄的第二章〈沒有藝術這回事〉中,「從這種意義上說,我認為藝術的範疇是由文化來決定的。」[2]
同時他還說了「沒有藝術這回事,只有藝術家而已。」[3],這個景象,我們多麼熟悉?在20世紀存在主義的卡繆「異鄉人」和卡夫卡的「蛻變」中,我們曾經孤立、蒼茫疑惑的被遺忘在兀自明滅著星光的宇宙之前,感受做為一個個體的渺小和蒼白虛無。而當時整個宇宙在自然科學家的研究室裡,正如火如荼的進行著碎形幾何的重新計算邊際,某部分量子物理學家則選擇在大膽假說中離開實證方法走向了哲學。個體面對浩瀚蒼穹的態度,也有著世代的和認知背景的差異。
在這個展覽中,藝術家運用了由錄影技術、電腦的數位控制、雷射激光設備、機械動力設備等,創造出多種形式下的影像媒介,並藉由這些影像媒介及所組裝的多媒體裝置,進行不同程度的「虛擬場域」的創造。在此借用「虛擬」來描繪藝術所創造的非現實場域,是必須強調觀眾常常透過被藝術媒介所生產的「幻境體驗」,激發出有別於現實脈絡的「新知覺」,這種新知覺的經驗過程,包含了藝術對話的目的和意義價值。藝術透過此種開顯知覺的方式,讓觀眾體驗一個隱藏在現實表象下的可能世界,個別作品所借用的特有通道僅提供部分的可能性提示,觀眾如何逐步洞穿表象的干擾,發現人類內在世界的共通場域,在對藝術家的「經驗還原」中,還原到自身之中。如同心理學家榮格的發現,經由文化母體、遺傳記憶等的潛在連繫,人類的內在存在著彼此相通的層面,個體只是在共同意識的儲存之海中提取片段組成各有特質的個體形式。
人與人間潛在的「根莖化」關係,在全球網際網路的連結中,被知識系統、物質科技視象化,同時又再次說明了數位化的虛擬世界來自於原本潛在的世界。但是以替代性的想像地圖去認知「存在的奧秘」,這種認知中存在著簡化的危機。因而藝術的創造中,為何總是不斷製造幻覺、不斷剝除幻覺,好比科學家也不斷提出「假說」、又再不斷推翻?因為當「虛擬」、「真實」這種相對性的爭執,在我們的文化階段浮現時,意味著兩者已經難以區分,兩者是同一件事的不同說法。「世界」的重要內容,將存在於「觀看」之中,被主體觀看,同時被詮釋、同時被記憶、同時產生影響力,這是當代文化在瞬間中的本質顯現。
影像媒介來自於科技文明,大腦的知識性語言生產了電腦語言控制系統,創造出的影像,有如在人類視網膜上顯現的「冷媒介」,藉助這種來自現實的「影像身體」,我們召喚腦中記憶與之對話。在展覽作品的對話中,我們感受到「影像身體」像「靈體」一般,便於分子化、傳輸、複製、重現,這種冷的介面語言,提供一種活潑靈活的表現方式,易於創造「幻境」,創造「新知覺」。猶如大腦在悠久的演化機制中,透過「影像」活動般的方式處理訊息,「影像」訊息可能較語言訊息更為原始。然而我們的自我究竟被主體概念支配或潛意識的驅力所迫?總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幻影」是脫離主觀意識掌握之物,但也往往是「觀看」之唯一媒介。
經由影像所創造的虛擬媒介中,最被人提及的「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其原初需求來自於電腦所建構的模型語言, 在電腦的螢幕世界中,重建人們熟悉的三度物理空間,透過「模擬」物理現實,達成跨國性的直接溝通。然而由於「虛擬實境」的用法,通常指稱特定實境的建構完成,因此在本文中,雖然不斷討論影像所創造的一種虛擬幻境或處境,卻以「虛擬場域」的形成,來指稱藝術家所創造的作品現場。
主體的變異與消失
最貼近於都會現實場景的作品,是王俊傑和郭亞珊的《微生物學協會:狀態計劃II》,貼近並且放大局部。作品借用劇中人物的主體面貌矛盾、多重,主觀時間和客觀時間衝突、多重空間重疊等的非敘述性影像內容進行都會人的內在描述,是本作品所掌握的「狀態」討論。而取用了台北縣市景觀中的捷運、電梯、樓梯、人行穿越道、證券交易所、餐廳和河堤邊等等交會性、過渡性場景,做為都會文本的取材之處。素不相識的男女主角在這些地方匆匆路過、暫時駐足,不斷處在行動和動作的片斷中,不僅面無表情,也無法提供行為本身的意義性。正是在這些取消了主體和行為意義之處, 反應著作者詮釋上的虛無特質,觀眾置身於被作者刻意強調的聲光多源的刺激之中,三個影片內容(微生物協會介紹以虛擬實境方式呈現、男女主角一日的都會影像拼貼)一開始即以虛擬的姿態呈現,觀眾幾乎不需透過感情的理解或想像參與,而是直接曝露在虛擬的、拼貼的影像訊息的包圍佔據中。王俊傑雖以慣用的都會元素拼貼方式結構作品,只是以往成果是反應消費幻想的「虛擬商品」,這次則矯稱為一種「虛擬研究」。
林書民的《窺—窗・系列作品1》也是一件近似都會現實場景的作品,從受訪者獨處經驗的訪問中切入,使得這件作品帶有社會寫實、心理寫實的觀看角度。因此當觀眾透過望遠鏡,一次只能看到一個「窗景」的一個時間片段,這種「切片」般的視覺經驗,是恰好回歸了作者以社會心理切片掌握都會文本的手法。展場空間的發光「窗景」和觀眾被設定在窺及被窺的狀態,使得「人」的形象,從個別性的降低、化為群體性的存在,有如被集體化制約和管理的對象,也許是作者對於都會人際的疏離和斷片化所產生的直接描述。劇中人從「被紀錄」化為「表演者」,個體的內在世界在外在表象的捕捉下,失去意義的價值脈絡,成為大量流失的無聲時間的綿延,也是都會虛無文化的一種寫真。
前述兩件作品有如以寫實性影像進行以影像為主的裝置,袁廣鳴的作品則恰好雖借用現實的影像素材,卻經由裝置狀態的轉換,將影像以非現實性的介面表現,突顯一種「異常」的描繪意象。在《難眠的理由》和《飛》之中,現成物床和鐘擺電視,都成為現場中劇場化燈光的聚焦所在,不在場的身體透過與身體經驗密不可分的影像內容,表達主體的內在世界,被念頭和腦內幻影所佔據的失眠者意象、籠中鳥的意象,都指涉著不在場身體內在清晰的知覺狀態,籠中鳥的脫困而出,不僅讓觀眾體驗物質性 介面的靈巧移轉,同時也使潛在的束縛獲得解放。
大陸藝術家馮夢波作品《潰客》,作者本身是網際網路上以虛擬身分對戰敵人無數的「衝浪者」(一般對於網路世界遨遊者的稱呼),這件作品來源於對戰內容片段的剪輯。但是,透過作者在本片中,進入虛擬實境世界訪問電子戰士,他們開展一段意味複雜的交談,叼著煙、行話不斷的進入網路無臭空間的馮夢波和虛擬電子人對談彼此彷彿沒來由的存在,其中「天堂是我們無助的幻覺,我們屈從它;地獄是我們敵人的象徵,我們毀滅它;社會是失去記憶的激情。我們為什麼在這?瘋狂!」,呼應著影片中以殺戮行動所開展的網路化空間,一切在行動中形成、開展,打破現代世界物理性的疆界,無座標的快速游移、穿梭、使既有空間解體,創造螢幕上滿溢的空間經驗,以及借助火光血光所激迸的流動性展現數位影像的新美學。無論是實體或虛擬的身體,在高度行動的爆發性狀態中,幾乎都以全然的瘋狂狀態回應世界。作者曾在創作自述中說「而真正能撼動我們的是遊戲之後的人們」,是否透過這個跨國人士匿名對打的現場,他感受到那是一個「沒有規則,只有現實」,只有存在的行動、沒有潛在方向諭示的世界的狀態?因而在本片的開始,他以類比影片的手法追憶著一個帶走人類明確情感的、慢速的過去時代?
新媒體影像中的語言焦慮
在前述的幾件作品中,藝術家所運用的影像語言各自來自不同的影像語言脈絡。例如,王俊傑過去的創作虛擬商品系列中,往往藉助於商業資本社會中,以視覺傳達手法為核心所創造出的影像化商品形象和幻想,衍生都會生活無盡的虛無感和人的意識的茫然狀態。在這次的虛擬研究中,王俊傑加強了對於主體自主意識「無用狀態」的描繪,主體有如精神分裂一般,被腦內此起彼落、都同樣真實(或虛幻)的念頭、幻影所佔據。藝術家並且運用強烈的影像訊息衝擊進入展覽空間的觀眾身體,觀眾在難以運用邏輯性思考的處境下,感受著藝術家所提供的「人性疏離」,影像語言的雜亂無章和暴力,使得都會人格的焦慮氛圍更為強化。藝術家以此凝結其藝術語言的形式和內容為一。
林書民過去的創作,通常以雷射全息攝影中蜷曲的人體、相互吞噬、再生的多族裔面容為「身體影像變奏」的核心。在影像身體的形成、轉換和流動間,身體的曲線從攝影的光影美學到有如律動的音符般重複、交響、變換,將原本各有意識的人類身體化為影像的視覺媒介,在此次的《窺一窗・系列作品1》中以介於紀錄和演出方式之間的狀態呈現,藝術家所慣常創造的移動性視點,以多螢幕的發光視窗替代;視窗中的人體,雖然彷彿有自主性,卻在獨處、被窺看的狀態中,置身於無意義的身體片段間,身體再度成為一種被視覺所追溯的虛無風景。無意義的焦慮感自視覺形式中瀰漫開來。
馮夢波結構性影片,也以多重、複雜、直接的影像本身,描繪著、討論著從「類比」進入「數位」之間的差異,「類比時代」的影音結合中,以帶有敘述能力的情感張力,進行與觀者的對話;而在「數位時代」所開啟的全方位行動和空間場域中,連瘋狂的殺戮也無須理由,一切均在指尖、神經末梢的快速震動下,建立新的遊戲規則。死亡在高速化、輕易化、影像化的界面下,輕而易舉。象徵生命形式的電子身體,不斷在畫面炸開,一種隱而不顯的知覺衝擊,透過藝術家複雜的影片風格潛伏著。
袁廣鳴曾在過去受訪的機會中,談到關於人類飛行的慾望,他說「但是無論如何,我們能做的只是不斷的墜落,或者是繼續相信自己能飛。」在科技技術的掌握中,他試圖表達人類獨特的感情和知覺,但是「事物總在一個難以彌合的差距中展現真實,虛影近似一種幻象。」
袁廣鳴的創作總是能夠透過白盤中游不出的美麗金魚、鳥籠中飛不出天地的鳥、床單上熊熊的火焰、汩汩流出的血跡,或在音箱震動中不斷重生、瞬即毀壞的自己的臉,展現著存在的掙扎,這種焦慮的內在,究竟源自何處?袁廣鳴有時會說,他痛恨電腦、科技性的多媒體,從所學到藉之為媒介,多媒體影像的運用中,包含紓解、也隱藏焦慮,究竟是語言(說話)幫助了我們,或再度囚禁了我們?藝術家穿透現實材質,抵達潛藏的世界,是否可能?
「世界」潛伏潛意識中?
美國藝術家Gregory Barsamian的作品《雙舞步》,藉由大型機動雕刻的方式創造出一 種令人驚奇的現場感。運用視覺暫留原理,以左右旋轉的金屬物件結構,結合閃頻器的強光,產生物體運動方向的錯覺,創造出物件變換的錯覺視象,提供觀眾一種有如幻境中的神奇視覺經驗,在作者的創作自述中曾提及最大的困難,在於如何選擇和觀眾的生活經驗有關的主題?藝術家透過這些他期望來自於潛意識或夢境中的物件,在三度空間和時間的幻覺透視中動態浮現,產生和觀者潛在知覺對話的機會。
在作者的創作自述中同時提到,他運用19世紀動畫技術,結合機械結構和物質屬性的基礎,創造出在一覽無遺的現場裝置環境中,一種黑白照片般「古典的」動態影像經驗,並且在動態的新關係中,他掌握住人類視覺所追求的秩序感,滿足觀看過程的驚奇性。運用影像達到視覺潛意識的愉悅和滿足,可以說是這件作品,最令觀眾激賞的因素。同時,也在這次展覽的類比式影像和數位式影像的對話中,替類比式影像做了強有力的表達。由於視覺錯覺僅在人類的視網膜上發生,使得這件作品彷彿以視網膜為螢幕,做了魔術原理的虛擬形象代言。
林俊廷作品《紀錄「零秒」》,則以時間的「歸零」、空間隧道的創造,體現一種觀眾經由身體參與、經歷心理知覺變化,所體驗出的作品。其中空間性身體經驗的產生,是來自於巧妙掌握雷射光與離子狀態的空氣結合產生的視覺「幻境」,在幻境中觀眾心理過程的虛質化和身體知覺的變異,成為這件形式單純的作品提供給觀眾的「知覺要素」。藝術家形塑這種知覺的過程,必須透過物理三維空間和第四維「時間」,在時間的經歷中,觀眾行經帶有視覺暗示的空間場域,完成「幻境體驗」,在「幻境」和現實的對照中,觀眾感受到現實中所可能存在的非現實縫隙。作者運用物質性材質,激發出能夠為人類所共有的視覺記憶或潛意識的起點,同時又結合視覺、帶給「身體」一種歷險式的變換過程,是這件作品能夠同時與觀者的意識和身體對話的耐人尋味之處。
日本藝術家市川平作品《有條件的樂園》,運用金屬和大型透明壓克力圓柱,創造一個由空氣驅動裝置、紅羽毛所形象化的視覺景觀。在這次展覽中,唯一不創造幻覺,卻在開放空間中,有如收納旅客陌生、好奇心理的轉化爐,以意象明亮的紅色,旋轉性的將視覺、心靈動線帶往高空,在其過往創作脈絡中所累積的—找尋工業性材質和廢棄器械的新美感知覺中,紓解了工業文明的焦慮感和科技形式的冰冷,產生一種機械動力作品的「熱介面」(經由藝術家主體情感的明確和藝術語言掌握的特質所形成)。放置於車站大廳挑高採光空間,成為旅客最初和最後接觸的作品,彷彿是整個展覽和板橋火車站的現實空間、意義上的一個重要轉化媒介。
在這幾位藝術家的創作思維中,多選擇呈現一種有別於現實的新可能情境,未從描繪都會現實的強大負面入手,並且在他們的作品和創作自述中,明顯的流露出對於潛意識世界的重視。如果我們將主觀意識視如水面浮冰,那麼水面下潛在的潛意識和集體無意識的龐大,將有更大的宰制力量。當代文化在脫離傳統秩序之後,呈現著一種多元、紛擾,多元詮釋座標未能重新結構的現況,同時在現代藝術所導入的現實揭露、 嘲諷顛覆等藝術手法中,人類曾經由藝術經驗到現代社會強大機制的非人性化—藝術透過暴力色情、慾望黑洞、腐敗美學描繪著時代。有如藝術所帶給觀者,意識和潛意識的撕裂、矛盾、焦慮,當代藝術是否可能嘗試藉由和潛意識世界的和諧對話,創造超越現實宰制的新境,突顯人類對於美好心靈生活的浪漫期待?藝術表達也在非對立性的語言表達中紓解了語言的焦慮感,在一種視覺奇境中,讓觀眾知覺到有別於商業影像訴求、藝術的無目的性本體?
開放語境中「隨機的」抉擇
置身後現代的處境中,藝術家面對當代文化的虛無,一般大眾和藝術遙遠的距離,以 及觀眾的慣性知覺被商業文明宰制的狀態,藝術的繼續存在以及對話都是困難的。藝術所揭露的真實經驗往往需要觀看者主動參與、在不確定的開放對話中交換內在知覺,還原出存在的複雜和真實,這樣的處境,常常正是一般大眾在都會生活中所刻意迴避、社會機制所樂於掩蓋的內容。在一個快速、強調商業生產效能的社會,藝術無目的性、慢速、無時間感的主體,有如驚鴻一瞥的夢境,予人驚喜、瞬即遺忘。
奧地利及法國藝術家Christa Sommerer & Laurent Mignonneau,則以其創作的一向風格脈絡為基礎,提出虛擬實境的人工生物環境作品《生命空間II》。在這件作品中,觀眾採取鍵盤為輸入訊息的管道,參與藝術家所創造的人工虛擬生態的生長發展。以英文字母為基因所組合出的造型和發音,給予所創造的人工生物一個「結合身體在內的命名」, 所造物雖然簡單,卻體現著「身體即感覺器官」的演化特徵,且彼此以其基因所決定的親屬關係衍生互動的機制。在藝術家取用生物學對世界詮釋的素材取材中,藝術家意識到將生物學中的「生命」—由基因、身體、生物的生態關係所詮釋—轉化為藝術造型上的「生命」。在藝術家的人工生物環境中,那些生物是以其「造型」和「命名」來做為主體,藝術家對話的介面已從科學轉化為藝術語言的介面。
這些來自生物學認知的生物,只被賦予有如腔腸動物般,直接單純的生命狀態,為了適應現實優勝劣敗和交配,不附帶情感、心理等的大腦神經中樞能力,可說是本展中體現章魚和水母浮游生物特徵的一種生物選樣。而觀眾扮演輸入這個開放性生態的外來動能和意志,一方面運用「字母」基因創造生物造型的「存在」,一方面無法擺脫生物生命基礎的特性和侷限。觀眾不期而遇的在此環境中和變種生物互動、共創未來, 是一個有趣幽默、能夠和遠離自然的都會人進行再度對話的人工生物模擬環境。
在這件作品中,將近年科學的主流議題,基因工程、複製、人工智慧朝向令人愉悅的人與自然新關係的建構中體現。在藝術的新媒體語言脈絡上,體現出這種語言階段的「語言自主性」特質,以開放生態中的生物,在電腦的亂數和參數的設定中,與觀眾互動而隨機生長。類似的語言媒介,在網際網路去主體身份的、隨機結合發展的創作形式中將會不斷衍生新媒體藝術的階段性特質,然而這兩位藝術家的風格中所重建的人和生物環境間的美學介面,將更加成為他們藝術的特有風格和能量。
顧世勇作品《輕,如何使自己更輕》,運用影像媒介創造了一個虛擬奇景,一種在孩提般輕盈的夢想中才可能存在的幻想。以現實取材的影像結合電腦3D建模,在原有的現實上,平滑地貼上一層新現實,這同時是承襲藝術家過往裝置創作的手法脈絡。在隧道型空間通道的底端,以鏡面反射所創造的影像光球巨大景觀,使觀眾彷彿從原本的現實空間,突然就抵達了宇宙的邊緣,不僅經歷視覺上高度的轉換,同時巧妙地將非現實性的輕盈夢想貼入現實,以一種零度狀態的創作自由,體現這件作品的精神景觀。觀眾隨著藝術家,在身體動能和潛能的激發中,以氣球飛昇,進入雄渾運轉不息的宇宙,在有限中經歷大我的無垠空間,成為一種難以言喻的心靈經驗。單一螢幕透過反射,複製出完整的充滿動能的光球,提供後現代的心靈,一種重新回歸整體的滿足。同時也體現著網路時代分子化的身體,能夠快速隨著主體的意念和行動,開展空間、開啟世界的自由可能。
這位藝術家在近年的創作中,透過多件作品的發展,傳達出一種期望超越理性概念思維侷限的創作知覺,嘗試經由主體的抉擇釋放意識的「緊張狀態」。並且藉由在現象世界之中開顯不可言喻的知覺,使存在回到「原初之域」的神秘可能性中。例如這件以童話、夢境或阿Q式的奇想,所開啟的敘事影像,帶給不同背景的觀眾,一個有意疏離於現實的歷程,現實的不可能化為可能,這種「身體」的飛昇,一方面是過去時代的「夢想」,一方面符合網路時代的身體詮釋—在「影像分身」的替代中,實踐虛擬電子世界的「烏托邦」。
法國哲學家梅洛龐蒂在「知覺現象學」中,曾經談到「活生生的身體是我們與世界相接觸的原始媒介」,有別於傳統藝術中身體與材質的結合形式,在顧世勇作品中,透過影像身體的「零度」經驗恰好體現了這個狀態。這種「零度」的體驗,一方面是作者掌握影像「冷介面」的準確性,一方面源自他所開放的世界探索,讓意義隨機組合。再借用梅洛龐蒂在「可見的與不可見的」一書中,所提及的「是存有在我們當中說話,而不是我們談論存有」,以及在「眼睛和心靈」一書中說「畫家常常發現自己與他們所畫的事物之間的關係是相反的,他們覺得『事物在盯著他們』。」正是因為在人類心靈潛在之處,存在著一種「觀看」,超越了肉眼的可見,直接望向了「不可見之處」。主體的開放意志,帶給人類和藝術有了和原初大地的存有直接對話的機會。[4]
數位時代藝術的影像虛擬語言,仍舊在以藝術家主體為核心的脈絡中發展。期待以客觀知識認知世界的科學,在這個意義上和藝術的態度是接近的;他們各自以不同的著重點觀看世界、描繪世界。科技工具從中性的狀態,演變出本身具有強大的物質屬性和能量,許多時候是脫離人的意志範疇而在世界中發展。針對影像媒介所建構的虛擬景觀而言,其中的空間本質已經改變,「以前的圖像可以說只是形象的再現:它是平面的,可能很逼真,但本質上是二維的。隨著虛擬圖像的出現,人們終於可以進入到圖像中去,它變成了一個場所,人們可以在裡面探尋,與別的人相遇,有虛擬的經歷。⋯⋯傳統意義上的空間—康德所說的空間—是經歷的先天條件:沒有空間就不可能有在其中的經歷。可是虛擬空間不同,它不是經歷的條件,它本身就是經歷。虛擬空間可以隨著人們對它的探索而產生。」 [5]
正是由於虛擬世界潛在於實體世界之中,因而它的出現是無遠弗屆的具有佔有性、必然空間。然而在當代世界,藉由知識力量所產生的「身體」,可以分子傳輸、複製再造,虛擬世界已能夠以脫離本源的方式,和本源的「原型」直接互動、相互改變。也經由這個虛擬世界的強大和真實,給予人類的潛意識龐大的負擔和種種焦慮性意象,當我們無所知覺的任主體意識和潛意識的矛盾撕裂我們,我們將失去精神安憩之所。藝術敏銳的指出時代的焦慮,也將避免自身成為新的焦慮循環的危機。
在當代新的科學認知中,曾經以一個蜷藏無限時間和空間在內的一個點狀結構,來想像宇宙的起源,宇宙的萬象,從一個瞬間炸開的點幻化出一切。在這個「一切皆幻、一切皆真」的處境中,人類意識、潛意識的本源儲藏,幾乎已成為觀看世界、演化世界的「基因」—行為的內在,意義重新結組的起點。
註釋
[1] 〈從發光異形到城市浮游—變形身體的意識與意志〉,2000,《從批判質疑到世俗想像—台灣的藝術與現代性討論會》論文集,梅洛龐蒂讀書會(Merleau-Ponty Circle)發行。
[2] 《藝術與科學—貢布里希談話錄和回憶錄》,(英)E.H. 貢布里希(E.H. GOMBRICH)著,楊思梁、范景中、嚴善淳譯,浙江攝影出版社。
[3] 同註2。
[4] 《梅洛龐蒂—現象學與結構主義之間》,詹姆斯・施密特(James Schmidt)著,尚新建、杜麗燕譯,桂冠圖書公司。
[5] 《技術帝國》(法)R. 舍普等著,劉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11。
文章出處
王品驊(2000)。失速狂喜:脫逃的章魚和水母。發光的城市:2000 北縣國際科技藝術展(10-17)。台北縣板橋市:北縣文化局。
展出記錄
[展名]:發光的城市—2000北縣國際科技藝術展
[展期]:2000/9/28~2000/10/29
[展地]:板橋火車站
[策展人]:王品驊
[展覽藝術家]:王俊傑、郭亞珊、林書民、林俊廷、袁廣鳴、顧世勇、市川平、葛瑞哥羅・巴薩米安(Gregory Barsamian)、克利斯塔・桑墨爾(Christa Sommerer)、羅倫・米諾奴(Laurent Mignonneau)、馮夢波
延伸閱讀
https://tcaaarchive.org/Keyword/Entry/1917
https://www.deoa.org.tw/project_content.php?res_no=17&cate_no1=&cate_no2=&ProjectYear=
關鍵雲
發光的城市—2000北縣國際科技藝術展、王品驊、王俊傑、郭亞珊、林書民、林俊廷、袁廣鳴、顧世勇、市川平、Gregory Barsamian、Christa Sommerer、Laurent Mignonneau、馮夢波、板橋火車站

.jpg)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