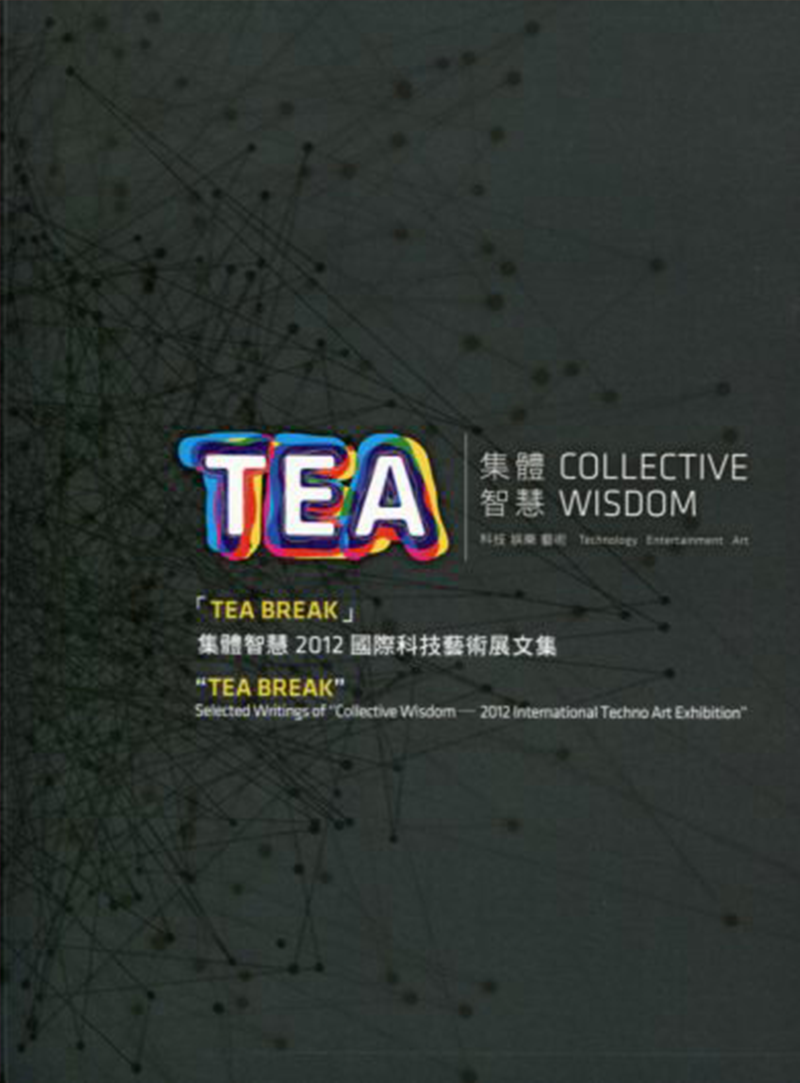2014國際科技藝術展
「奇幻視界:當代影像景觀的形變」
作者/策展團隊
「奇觀並非影像的聚積,而是經由影像中介之人與人間的社會關係。」
(居伊.德波,1983,《景觀社會》)
始自於十九世紀,視覺經驗技術化(technologicalization of visual experience)的浪潮不僅拓展了人們的視覺領域(visual horizon),更將視覺經驗變成了商品,這些新的視覺文化非但重塑了人們的記憶與經驗,連同日常生活都被社會的影像增值給改變了。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在《世界圖像的時代》(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中便曾指出,從本質上看來,世界圖像並非只涉及一幅關於世界的圖像,而是指借助於技術,世界被掌握成圖像,因而被視覺化了。[1]爾後,居伊.德波(Guy Debord)以「景觀社會」(the society of spectacle)的論點,訴說著「真實世界已變成實際形象、純粹的形象以轉換成實際的存在」且「在現代生產條件蔓延的社會中,其整個生活都表現成為一種巨大的奇觀積聚,曾經直接地存在著的所有一切,現代都變成了純粹的表徵」。[2]換言之,奇觀將每個人的物質生活變成了一個靜觀的世界。
1990年代之後,動態影像伴隨著越來越多數位媒體的技術,不論是具象或抽象的創作皆大舉進入到藝術展演空間,出現在相關藝術展出之中。在許多作品裡,其以裝置的方式呈現,將影像的時間性「空間化」(spatialization of the image temporalities),影像透過在多元創製與投映方式,被安置於空間裡。[3]此外,影像也從固定的展示場景(客廳中的電視、電影院、博物館)進入到流動的開放場域;同時,螢幕也不再只是固定的框格概念,當影像開始投映在各式各樣的載體上,甚至進入城市空間時,螢幕的框線已然消失,建築物、天空,或是自然景觀則成為展示影像的巨型布幕。當影像跳脫固定的螢∕銀幕框格,從媒體展示器上出走,進入城市空間甚至無限寬闊的天際,並以各種奇觀之姿湧向消費者或城市漫遊者時,人們觸目所及似乎是無限大、無限多、無固定載體的影像世界。
另一方面,隨著各種數位科技(尤其行動科技)的發展,影像卻又必須仰賴行動科技的小螢幕才能遊走於城市空間。因此,影像不僅從室內走向戶外,影像載體也從螢幕逐漸邁向無螢幕的城市景觀,如今更隨著行動裝置的小螢幕穿梭於城市空間。
具體而言,影像在數位時代裡並非「一個」(one)影像,這意味著它並不存在著一個可以與它自身相對應的存在。甚至,在電子螢幕上輸出這些影像也不斷的混淆我們對於影像究竟「是」什麼的理解。換言之,電子影像是一種以時間為基礎(time-based)的影像,這並不僅因為它擁有接續(succession)的能力,更因為它並非完全呈現在空間或時間裡;它佔有一種持續處於當下不斷生成變化的狀態(a state of continuous present becoming),而數位影像不斷處於變動之中或處於動態變化的狀態,即使它們看起來是靜態的。以致,一個數位影像的本體結構已然成為一個不斷轉變的或自我更新(self-refreshing)的展示影像。就此而言,數位影像不僅挑戰了我們對於影像的一般理解,同時也挑戰了物件或美學客體是如何靜態的處於時空之中。就某方面而言,並沒有所謂的新媒體「物件」(objects)或影像,「元素」(elements)或許是一個比較適切的辭彙,它可能因為輸出的方式或運算邏輯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樣貌。因此,數位音像藝術所涉及的並非某個物件的製作,而是一個訊號(signal)在處理過程或轉變過程中的各種變化。
以致,當代社會是一個被影像、符號與視覺化的語言所圍繞的生活。動態性資料的視覺化允許我們去瀏覽影像與文字形態的資訊,並經驗其變化。而觀看的經驗是奠基於身體感知作為有表達意識主體之上的傳播行為,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便認為,姿態的感官並不是被給予的,而是被了解的;換言之,是在觀者角度上的觀看行動。[4]觀者的觀看行為將物質世界與虛擬數位世界中再現的影像,透過其感知接收與表現的活動連結在一起。當觀者專心致力地觀看著多元的數位藝術作品時,其有意義的主體身軀已經和界面連結在一起;數位藝術所應用的介面媒材也因此在奇幻的影像景觀(fantastic image-scape)中被局部穿透了。然而,觀者必須自覺的是,觀看的過程是對介面的凝視,而非看穿界面。當我們將影像的載具當成是一個開啟虛擬世界的窗口時,這個世界便是透過數位科技所呈現出來的視覺化世界,也正因為這個視覺化的世界是藉由數位科技所構築而成的;於是,數位美學的感官經驗無法忽略這個科技的界面與主體身體與感知之間的關係。傅柯(Michel Foucault)便呼應了梅洛龐蒂的觀點認為,視域(vision)必須在現象學的概念之上被理解,因為唯有透過身體主體與世界的互動才能真正地理解視域在生活空間經驗中的意義。[5]由於知覺本來就是發生在身體的與感官的層次,所以,微觀知覺本來就已經具有意義了,因為進行知覺與感覺的身體一直是一個活生生的身體(lived-body),也一直在創造社會意義。因此,觀者便透過其多元的互動經驗,使其成為瀏覽者的角色;而影像亦成為傳播過程中愈來愈符合人工智慧的視覺化空間。
由此可知,當我們透過科技而進行觀看時,我們不僅只是看到了科技所呈現的影像,我們更是科技性地進行觀看(to see technologically)。以當代的投影(mapping)影像為例,其視覺特性與影像的移動,讓人們可以看到一種在視覺上不可能出現的現象:我們同時是有意向的主體,也同時是這個世界裡的一個物質性客體,我們既是觀看者也同時是被觀看之物。[6]這意味著電影作為一種客體現象是因為在觀看視覺的過程中,觀者因為這些數位視覺影像而轉變成主體;然而,他們也同時是那些被再現的客體。因此,對於數位科技文化的詮釋,不該僅關注於再現的面向,也不該忽視科技的物質性,更應該探究體現主體如何透過科技進行知覺,並且在知覺的過程中,體現主體與客體現象之間是如何相互建構。這樣的影像敘事呼應著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所認為,在新的模仿時代之中,我們已邁向社會發展的全新時代,甚至超越了奇觀社會及其遮蔽的面具,宣稱與現代性生產體制的告別,進入在擬像的世代。於此世代中,真實被本質的,或模仿的事件替代,電子或數位影像、符號或景觀替代了真實的生活與真實世界中的物。擬仿模式產生了幻象以作為真實的替代品,且無所不在。以致,幻象(Illusion)成為真實世界的單純符號與圖像,它組成了一個「超真實」(Hyperreal)的新視覺經驗領域。[7]
當自然界與所有相關事物都被科技和自我指稱的符號全面替代之際,人們可以發現,在一個主客體具體被抹去的世界裡,語言不再與牢固的意義相互構連,當獨立的客觀世界被吸收同化被界定為人造代碼和擬仿模式時,充滿著所有不同意願和目的的真實世界被征服了,正如德波所言,社會生活本身已經成為景觀的累積,所有曾經直接存在者均已被再現,早期資本主義社會將人類經驗從「存在」轉為「擁有」;而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則是將「擁有」轉為「陳列」。有鑑於此,本展以「奇幻視界」(Wonder of Fantasy)作為命題,透過連結物質世界與虛擬空間的體現式視域(Embodied Horizon),窺見「Mapping」作為數位科技與視覺藝術跨域的橋梁,提供觀者各種了解空間、影像與主體之間關係的方式,在一個奇幻視覺叢林中,人們見識了奇幻的(Fantastic)「蒙太奇空間化」(Spatialisation of Montage)的投映表現。[8]本展期盼透過來自於世界各國的國際藝術家創作,以及臺灣數位藝術創作新銳的作品,以不同的投映技術、影像載體、視覺造型等多元面向,期盼觀者見識到「景觀社會」已經邁進一個新的階段,從一個傳統可以和諧、分離、重疊、爭論、連續或不連續的想像和意義鏈結的視覺表徵外,更透過影像將想像世界和圖像意義製造的經驗透過裝置及其資訊的增加而增強,進而展現視覺圖像化的蒙太奇效果,為影像注入了另一個空間存在面向;而空間面向的凸顯,讓觀影不再僅是存在於觀者與影像之間的活動,更必須將展場空間(特定的建築空間、美術館等)納入影像思考脈絡。
後數位景觀社會
近來在討論數位技術與藝術實踐的種種現況時,「後數位」(Post-Digital)是一個經常被提出的概念。這個詞彙其實並非直到現在才出現,至少在2000年的時候,新媒體藝術家羅伯‧佩波羅(Robert Pepperell)與麥可‧龐特(Michael Punt)即合著過一本名為《後數位之膜:想像、技術與欲望》(The Post digital Membrane: Imagination, Technology and Desire)的書,將當時勃興中的數位技術、人類想像力與藝術創作,進行清晰有趣的案例分析。在上個世紀末的當時,他們提出面對不斷加速技術演進的數位時代,人們自此無法脫離on/off、0與1的世界,進而從人的基本需求與反應為中心,提出後數位時代的願景。其中羅伯‧佩波羅更是早在1995年即出版過《後人類狀態》(The Post-Human Condition),探討人類與科技不斷提高共生狀況的現實。十餘年之後的現在,許多評論者開始將後數位視為當代,而將數位推擠到過去式的討論範圍。在不同創作類型的領域中,常常對數位技術帶來的便利性已視為當然,並同時聲討其無新意與魅力喪失的缺失。以音樂為例,電子音樂家金‧卡司柯尼(Kim Cascone)的著作《失敗的美學》(Aesthetics of Failure),引用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的創辦人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Nicholas Negroponte)所言:「數位革命已經結束」,西方世界與好萊塢已經以商業手段打包帶走了。這些來自第一線創作者的意見雖然不是定論,卻是非常具有建設性的質疑,因為他們正是最接近數位技術與藝術創作的專家。在這些例子當中,羅伯‧佩波羅在90年代即受邀於奧地利林茲電子藝術中心展出,金‧卡司柯尼則參與了大衛‧林區(David Lynch)電影《雙峰》(Twin Peaks)的音樂創作,都不是外行人在圈外的生疏臆想。這些討論無法一一列舉,但都有類似的態度,一致指向相近的焦點,即作為人的意義及重新思考的必要性。
《媒體考古學》(Archaeology of Media)的作者西格弗里德‧齊林斯基(Siegfried Zielinski)曾回應一個問題:新媒體真的新嗎?(Is New Media Really New?)他在1999年接受電視訪問時,曾經提出一個人類文明進程的淺白立論,即:此刻的我們並非完全創新,而是在歷史累積的基礎上緩步向前,朝向未來,數位科技亦是如此。身為新媒體藝術的前衛學者,有趣的是,他並不看重一般以為新媒體藝術應該具有的互動的特質。關於互動,他認為是一連串被設定的程序,本身並無關藝術,甚至有害於藝術表現的多樣性。能讓觀者隨意選擇不同的可能性、自由組合,一直是自從超文本標示語言(Hyper Text Markup Language,HTML)觀念普及廣泛應用之後,被視為時代特色與數位藝術的強項,並加以推崇。但他卻一語道破其中的弔詭,也就是說,看來廣泛、難以數計的互動選項,其實是在觀眾與作品之間有限制的變化,是無稽的,甚至於對藝術有害。他進一步解釋數位與類比在性質上如何區別的問題,簡潔有力指出了:數位技術是被發明來避免錯誤,它可以創造完美的計算,基本的特質是「正確」。然而演化與創造行為卻與此相反,錯誤與混亂常是必須的。西格弗里德‧齊林斯基認為數位在生活中許多面向並不夠強壯,相反的,類比的熱情與非理性的力量更可以依賴。
數位技術與顯示介面的高度發展,雖然提供了細緻模擬自然的視覺介面,背後仍然是一連串複雜不容錯置的指令,完全不離正確計算的功能。當計算功能提高數千萬倍的反應速度後,提供了人的感知經 驗無法察覺順序的指令,而被我們視為同時並存的多樣選擇。事實上,它所提供的只是容量有限的分類路徑,選擇即便看來目不暇給,仍然是有限的組合。而類比或自然現象,一開始就提供完全無限的可能性,但無法重複與保證正確。非理性的熱情與理性的技術經常是不相容的,而新媒體核心價值就必須建立在不斷更新與反思的精神性辯證之上。或許,我們必須努力的是將非理性、熱情的力量,置入理性的邏輯與機械技術之中,創造出數位與類比的全新融合。
近半個世紀之前,居伊‧德波(Guy Debord)出版《景觀社會》(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創造了「景觀」(Spectacle)的概念,作為資本主義發達社會危害人類精神的原點。像所有的前衛思想一樣,他的基本主張是反藝術、特別是與真實生活脫離實際聯繫的藝術生產。因為作為愚弄人類的手段之一,由資本主義源頭所生產的一連串限制性影像符號,最終將使人類真實情感的表現,都被限縮在有限性的影像或詞彙裡,徹底被統治而不自覺。將這些主張拿來與現況作對照,在邁入後數位時代的此刻竟然並不顯得陳舊,反而是更加生動的描寫,彷彿是在現場的陳述。因為他所反對的情況一直都沒有本質性的改變,尤其在數位技術完全融入生活之後,相對應的控制手段更加精密與難以擺脫,這些軟硬體工具被用心製造成精品的樣貌,安靜無害遞送到我們的手上,讓我們樂於收納展示且愛不釋手。在很短的時間之內,所有的人都迷上了智慧手機指尖點選滑動的互動行為,專心膜拜的樣子彷彿形成了一種集體催眠的奇觀。其中的聲光內容、資訊傳遞與回饋方式,正如同居伊‧德波所憂心的未來,人們使用著被預先設定好的貧乏詞彙溝通著,並表達出誤認為是出自於自己感受的意見。沒有人有機會能阻止這種情況持續發展,因為數位技術現在已經取得大多數人的信任,從人的助理演變成人的代理,但是基本上,使用者選擇權(Opt-in/Opt-out)的闕如正是自由社會的反向指標。
除了上述的嚴重缺點之外,剩下都是眾人皆知的優點。持續創新的技術確實提供了最多的機會,前所未有的在藝術領域裡作為創作工具的代表。藝術家也跟一般人一樣,身處在這個後數位景觀社會之中,無法獨自創造出另一個世界,但藝術家卻應該擁有更敏銳的觀察力與行動力,滲入這個被數位技術層層羅織的網罟,作為典範轉移與反抗的先鋒,而不是加入景觀的生產線。藝術家也是樂觀的批評者,但只能以藝術作為反藝術的武器。媒體變體學(Variantology of Media)的研究指出,偶一出現不合時宜的發明,在另一個時空下可能啟發、改變了媒體常態發展的歷史。在數位藝術即將成為老詞的現在,也應該是群魔亂舞的浪漫時代,以便向後世證明我們並不怠惰。
偏見即主張。在藝術的領域裡,我們無法提出周延的論述,只能將自己內心的想法老實說出來。
註腳:
[1]吳瓊,〈視覺性與視覺文化—視覺文化研究的譜系〉,《視覺文化的奇觀》。北京:中
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頁12-13。
[2]Debord, Guy. The Society of Spectacl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Detroit: Black & Red, 1983. p.12.
[3]Steetskamp, J. (2009). “Moving Images and Visual Art: Revisiting the Space
Criterion.” Cinéma & Cie, 9(12), pp.65-70.
[4]Merleau-Ponty, Maurice.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Trans. C. Smith.
London: Routledge. 1962. p.185.
[5]Jay, Martin, Downcast Eyes: The Denigration of Vision in Twentieth-Century
French Thought. California: Berkeley, 1993. pp. 386-387.
[6]Sobchack, Vivian. “The Scene of the Screen: Envisioning Cinematic and
Electronic Presence,” Materialities of Communication, ed. by H. U.
Gumbercht & K. L. Pfeiffer,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83-87.
[7]參見:Baudrillard, Jean.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5.
[8]Kotz, Liz. “Video Projection: The Space between Screens.” Art and the
Moving Image: A Critical Reader. Tanya Leighton eds. London:Tate, 2008.
- 372-373.
展覽資訊:
[展名]:奇幻視界 – 2014國際科技藝術展
[展期]:2014.5.17~8.3
[展地]:國立臺灣美術館101展覽室
[策展人]:邱誌勇、張賜福
[展覽藝術家名單/國內]:李柏廷、沈聖博、王連晟
關鍵雲:奇幻視界 – 2014國際科技藝術展、李柏廷、沈聖博、王連晟